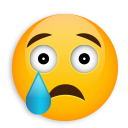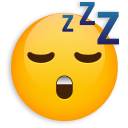12399456https://www.upal.com.my/zh/feeds/jobFeedKwongwahArray
(
[0] => HTTP/1.1 200 OK
[1] => Date: Fri, 23 Jan 2026 19:46:10 GMT
[2] => Content-Type: text/xml; charset=utf-8
[3] => Connection: close
[4] => Cache-Control: no-cache, private
[5] => Cache-Control: no-cache, no-store, must-revalidate
[6] => Set-Cookie: UpalLiveSession=eyJpdiI6InFUVng0dFNFOGtzNHVZZUxRRFZkVlE9PSIsInZhbHVlIjoiTU41b1FZSCtMZTQ4THliUDM1czRJOFJ1VjBRbUc2YUtNWGRvdzhQM3dza25VYVduTkVRQmt1UU05K1pCRzdCTXdpVVN0OVVPRlBmVU9KZlRwY0U1S3c9PSIsIm1hYyI6ImY0MjU1MzgwM2E3OTlmZDJmNzY4NTFiNmNjN2FkNmIyMGUyZTg1YmYwMDA3NmQwODM2YmVlYzUyOTI5YmU4OWMifQ%3D%3D; expires=Mon, 22-Jan-2029 19:46:10 GMT; Max-Age=94608000; path=/; HttpOnly
[7] => x-frame-options: SAMEORIGIN
[8] => x-content-type-options: nosniff
[9] => x-xss-protection: 1; mode=block
[10] => referrer-policy: strict-origin-when-cross-origin
[11] => permissions-policy: geolocation=(), microphone=(), camera=()
[12] => content-security-policy: default-src * 'unsafe-inline' 'unsafe-eval' data: blob:; script-src * 'unsafe-inline' 'unsafe-eval' data: blob:; style-src * 'unsafe-inline' data:; img-src * data: blob:; font-src * data:; connect-src *; frame-src *; object-src *; media-src *; child-src *;
[13] => Server: cloudflare
[14] => x-robots-tag: noindex, nofollow, nosnippet, noarchive
[15] => strict-transport-security: max-age=31536000; includeSubDomains; preload
[16] => expires: Sat, 24 Jan 2026 19:46:10 GMT
[17] => vary: Accept-Encoding
[18] => Report-To: {"group":"cf-nel","max_age":604800,"endpoints":[{"url":"https://a.nel.cloudflare.com/report/v4?s=8KlLBLavyhn4H7TTcEAnQG7pOdGqyzhMgU93HMlIcTUrQ%2F60NFKUtHq70Z7r42sE1fhYi%2Bw%2Blg2kL7Nd%2BWS5s%2Bf7pRsQdybywa%2B4rR79zQ%3D%3D"}]}
[19] => cf-cache-status: DYNAMIC
[20] => Nel: {"report_to":"cf-nel","success_fraction":0.0,"max_age":604800}
[21] => Speculation-Rules: "/cdn-cgi/speculation"
[22] => Server-Timing: cfCacheStatus;desc="DYNAMIC"
[23] => Server-Timing: cfEdge;dur=6,cfOrigin;dur=103
[24] => CF-RAY: 9c29cbada8954e66-SIN
[25] => alt-svc: h3=":443"; ma=86400
)
789
文:董恪宁
上古之时,先民相信,灵魂不朽,元气永在。一个人在世所有的那一身躯壳,只是外在寄生的皮囊;纵然不幸离世了,他的灵魂犹存。因为这样,世界各地,多有一套守墓之习俗。
何解?城市历史学家Lewis Mumford 在名著《The City in History》揭示,古人恐惧灵魂,定居墓旁,渐成部落;十百千万,风俗间接促动百姓长期留守当地,构成城市之雏形。
Lewis的学说认为,纵然守丧的期限过了,儿女通常继续留守周遭。分布当地,疏疏落落的人家随之渐多,最终形成一个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小镇。我们现在追溯历史,当可发现这点。随着时间的不断推前,原在郊区的墓地,甚至划入了城市的边界。
孔子既逝,亦然如此:门下弟子服丧三年,分守师墓,“三年心丧毕,相诀而去”;“唯子贡庐于冢上,凡六年,然后去”之感人事迹,因此广为流传有情人间,成为孝道的经典之作。
全球的许多大都会,皆有类似的佐证。先后怎样,都不重要。总而言之,墓园不但属于城市结构的重要部件,也是组成信仰和心灵的要素。慎重追远何以传承至今,也就思之自明了;清明的祭奠,缘由在此。
按照《孝经》之言,哀戚之心,不仅是在外在的“哭不偯、礼无容、言不文,服美不安、闻乐不乐、食旨不甘”;同时也在“擗踊哭泣,哀以送之;卜其宅兆而安措之;为之宗庙,以鬼享之;春秋祭祀,以时思之”。
然则,儒家传统的教诲所示,这一切还是其次的。孝道的根本彰显,不在灵堂,而是色难。《论语》孔子应答子游问孝,最能反映这点:“今之孝者,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,皆能有养;不敬,何以别乎?”
宋朝大儒欧阳修的〈泷冈阡表〉自言家世的坎坷,所表达的也正是这一层的意思:“祭而丰,不如养之薄也。”那么,诚如《韩诗外传》所言:子欲养而亲不在,自然是空遗恨了。
反之,有心则灵,外在的那些繁琐的一系列仪式,不管有多隆重,其实还在其次,既不必纠结,也无需拘泥。否则,遵照古礼,不但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,我们也许还得墨守祖墓,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。
理解这些,处理眼下的左右为难,自然容易多了。此时此刻,病毒逞凶肆虐,疫情嚣张跋扈,病例变本加厉,显然的是,不得不有所权宜之变,再也不可能一如既往地前往扫墓。
缘由所在,浅显不过,孝道之本,首在自爱。“立身行道,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”,不管是孝之终也;根本的环节,乃是确保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”。
既然这样,面向这一场相等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瘟疫,每个人的保身保命,才是不能退让的底线。思及这点,传统所行,自然可以容后再办,迟些处理。先祖有知,必然也会体谅子孙当下的非常无奈。
民俗学者李永球先生点示之道,确是智者的见地:模仿南来的前人,对空遥拜,心诚则灵,有孝天知。听起来,当年虽然没有网络配套,其实已有“远程祭神灵,在家拜祖先”这一套。视频广播自己的孝心过人,则大可不必了。
找工作, 就找这里!

› 立即申请
- GMBB Part Timer
- Event
- Kuala Lumpur
-

MYR 11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Social Media Marketing Executive
- Advertising & Market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6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Software Develop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Wilayah Persekutuan
-

MYR 6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DevOps Software Engine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6.5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Java Software Engine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10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Software Engineer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4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Web Developer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4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Software Engineer (Internship)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Software Develop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4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HR Recruiter (Internship)
- Human Resources
- Kuala Lumpur
-

MYR 85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Web Developer (Internship)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Multimedia - Video & Marketing (Internship)
- Advertising & Market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Admin cum Customer Service
- Engineering
- Bayan Lepas
-

MYR 3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Graphic Design + Marketing (Internship)
- Advertising & Market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软件测试与客户支持专员 Software Testing & Customer Support Specialist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3K /Month
//
//
//
/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