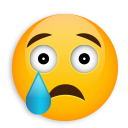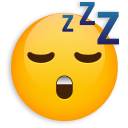12399456https://www.upal.com.my/zh/feeds/jobFeedKwongwahArray
(
[0] => HTTP/1.1 200 OK
[1] => Date: Fri, 23 Jan 2026 21:30:20 GMT
[2] => Content-Type: text/xml; charset=utf-8
[3] => Connection: close
[4] => Cache-Control: no-cache, private
[5] => Cache-Control: no-cache, no-store, must-revalidate
[6] => Set-Cookie: UpalLiveSession=eyJpdiI6IlwvMCtXTGtRMjBwWnNcL3BLdjh3ajd2dz09IiwidmFsdWUiOiI5d0ZqNlc2bDUzRVNndWV5ZTArYjZ4NjBOeGg1b0ZDTFNpK1pXTFg4Y29IZUVqXC9md0pSXC9oK294NGFjTXc0YldEbjhtendkazg3cEVSVFRMK2l5eW5nPT0iLCJtYWMiOiI3MjgwMTcxOTdjNzg3ODdjMzc5ZmM3NzQ1Zjg4N2VmMjQ0YWZkMzdhZjk1MGZmNTQzNDk4OGNkODE4NGYxZjQ3In0%3D; expires=Mon, 22-Jan-2029 21:30:20 GMT; Max-Age=94608000; path=/; HttpOnly
[7] => x-frame-options: SAMEORIGIN
[8] => x-content-type-options: nosniff
[9] => x-xss-protection: 1; mode=block
[10] => referrer-policy: strict-origin-when-cross-origin
[11] => permissions-policy: geolocation=(), microphone=(), camera=()
[12] => content-security-policy: default-src * 'unsafe-inline' 'unsafe-eval' data: blob:; script-src * 'unsafe-inline' 'unsafe-eval' data: blob:; style-src * 'unsafe-inline' data:; img-src * data: blob:; font-src * data:; connect-src *; frame-src *; object-src *; media-src *; child-src *;
[13] => Server: cloudflare
[14] => x-robots-tag: noindex, nofollow, nosnippet, noarchive
[15] => strict-transport-security: max-age=31536000; includeSubDomains; preload
[16] => expires: Sat, 24 Jan 2026 21:30:20 GMT
[17] => vary: Accept-Encoding
[18] => Report-To: {"group":"cf-nel","max_age":604800,"endpoints":[{"url":"https://a.nel.cloudflare.com/report/v4?s=%2BAkWf%2F0WlFBZhfCjFpixLsYORufc%2FJKVSEi9tWuujh7Qe5hCRshUyxr0sjBj%2FwarBoWnpP%2FB%2Bk%2F0ri7P4AKSOyiA449G1MDEP%2FRWyzrT8Q%3D%3D"}]}
[19] => cf-cache-status: DYNAMIC
[20] => Nel: {"report_to":"cf-nel","success_fraction":0.0,"max_age":604800}
[21] => Speculation-Rules: "/cdn-cgi/speculation"
[22] => Server-Timing: cfCacheStatus;desc="DYNAMIC"
[23] => Server-Timing: cfEdge;dur=8,cfOrigin;dur=157
[24] => CF-RAY: 9c2a6445cd0c3def-SIN
[25] => alt-svc: h3=":443"; ma=86400
)
789
文:董恪宁
晚清年间一张张老照片,入镜的是一道道大相径庭的两极风景:一边是正襟危坐的朝官,展现威武升堂的气势;一边则是吸食鸦片的男子,懒洋洋窝在床上,沉溺幻觉之中,一脸的感觉良好。
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,自古皆然。唯民间贫困人家,不比T20的家庭,一旦不幸陷入毒海的泥沼,卖了妻儿,比比皆是。而一品的大官,瘾毒人心,渐不成形,排队沦为萎靡不振的东亚病夫。
可惜,上奏的情报,往往都是夹带洋洋洒洒的不吝溢美之词;大事化小,小事化无。等到后来遽然发现举国皆毒,已经晚了。《清史稿·卷三百六十九·列传一百五十六》记林则徐之事迹,也正是这么一回事:
(道光)十八年,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鸦片烟,下中外大臣议。则徐请用重典,言:“此祸不除,十年之后,不惟无可筹之饷,且无可用之兵。”宣宗深韪之,命入觐,召对十九次。授钦差大臣,赴广东查办……
林则徐一身都是忠臣的DNA,领旨遵令,雷霆万钧,尔后所行皆是玩真的:严申禁令,整兵严备;檄谕英国领事义律查缴烟土,驱逐趸船,呈出烟土二万馀箱,亲莅虎门验收,焚于海滨,四十馀日始尽。
置喙造句,可见当时的毒风之盛,确实难以想象。何况,除此冰山一角,粤东走私极之严重,福州、厦门,也建有不少秘密管道输送。层层叠叠,康雍乾盛世的八旗子弟,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
云贵总督沈秉堃在上呈朝廷的〈奏查明大员吸烟情形据实覆陈折〉之折,奏明贵州的大臣庞鸿书、藩司松鄂、学司陈骧、臬司严隽都“以大瘾著称”。既然如此,到了下面,夷烟流毒,处处都是;那还用说?
风气渐靡,后来林则徐的心意似乎也有所动摇了。有学者援引历史档案称,1847年初,林则徐一度经如此这般答复文海:至于变通之说,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。暂且不论林氏所言的脉络如何,据此可见,沉痾宿疾,变本加厉。
总的来说,种种迹象,尽是就将亡国的征兆。《末代皇帝溥仪自传》里,坦述了堂堂的末代皇后婉容亦沾染了毒瘾。知书识礼,雍容大度,自署“伊丽莎白”的婉容,自此精神病态,烟容灰绿,喜怒无常,生不如死,最终病逝在牢狱之中。
婉容的悲剧,不是大清王国唯一的感伤。紫禁城的里里外外,全是类似的画面。鸦片是这个王朝最后的辉煌。唯有烧起这一圈圈短暂的袅袅烟火,宫廷的遗老才能看到一丝的火红希望,因此坚信他们还是这片江山的主人。
可是,世界变了。自自闭的乾隆天朝,工业革命的号角,陆续吹遍欧西的大城小镇。锋刀利剑,不管用了。真枪实弹才是硬道理。借助赔款出走海外留学的精英,逐步体验了这个事实。可惜,前排的当权领导偏偏不思长进,仍然装睡。
晚清不是一个历史的时间点,而是国力的代词,也是企业的借镜。因为晚清的鸦片,我们看懂了,堕落是每个王朝必然的末路,麻醉则是每个命官沉沦的开始。水银灯下,他们追逐瞬间的欢乐和亢奋,门外鳏寡孤独的悲凉,就别提了,那多扫兴。
找工作, 就找这里!

› 立即申请
- GMBB Part Timer
- Event
- Kuala Lumpur
-

MYR 11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Social Media Marketing Executive
- Advertising & Market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6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Software Develop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Wilayah Persekutuan
-

MYR 6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DevOps Software Engine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6.5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Java Software Engine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10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Web Developer (Internship)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Software Engineer (Internship)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Admin cum Customer Service
- Engineering
- Bayan Lepas
-

MYR 3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Graphic Design + Marketing (Internship)
- Advertising & Market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HR Recruiter (Internship)
- Human Resources
- Kuala Lumpur
-

MYR 85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软件测试与客户支持专员 Software Testing & Customer Support Specialist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3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Multimedia - Video & Marketing (Internship)
- Advertising & Market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Software Develop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4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Software Engineer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4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Web Developer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4K /Month
//
//
//
/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