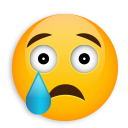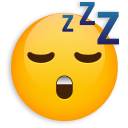12399456https://www.upal.com.my/zh/feeds/jobFeedKwongwahArray
(
[0] => HTTP/1.1 200 OK
[1] => Date: Thu, 05 Mar 2026 00:20:56 GMT
[2] => Content-Type: text/xml; charset=utf-8
[3] => Connection: close
[4] => Cache-Control: no-cache, private
[5] => Cache-Control: no-cache, no-store, must-revalidate
[6] => Set-Cookie: UpalLiveSession=eyJpdiI6InE2dHlZNUZmZ0FWbktySFN0V0dhUFE9PSIsInZhbHVlIjoia3pLazBUQ1B4TklSK005c0lWcFZmRXozb1FPbkExb3J0WU5vTDN4dFpkZm1mNm1oY3o5Q0lDNUU5aGR4MkNJQVlYbno5dDdMakZKdUhLT0pyT09XM3c9PSIsIm1hYyI6IjhlYjJiYTQ4ODBjNmEwOTFlNzk0NTIwZWMzMmRkODE5OThkNjMzOTBjYjZlNmMwYWExY2ZkMjBkNDQzM2IzODkifQ%3D%3D; expires=Sun, 04-Mar-2029 00:20:56 GMT; Max-Age=94608000; path=/; HttpOnly
[7] => x-frame-options: SAMEORIGIN
[8] => x-content-type-options: nosniff
[9] => x-xss-protection: 1; mode=block
[10] => referrer-policy: strict-origin-when-cross-origin
[11] => permissions-policy: geolocation=(), microphone=(), camera=()
[12] => content-security-policy: default-src * 'unsafe-inline' 'unsafe-eval' data: blob:; script-src * 'unsafe-inline' 'unsafe-eval' data: blob:; style-src * 'unsafe-inline' data:; img-src * data: blob:; font-src * data:; connect-src *; frame-src *; object-src *; media-src *; child-src *;
[13] => Server: cloudflare
[14] => x-robots-tag: noindex, nofollow, nosnippet, noarchive
[15] => strict-transport-security: max-age=31536000; includeSubDomains; preload
[16] => expires: Fri, 06 Mar 2026 00:20:56 GMT
[17] => vary: Accept-Encoding
[18] => Report-To: {"group":"cf-nel","max_age":604800,"endpoints":[{"url":"https://a.nel.cloudflare.com/report/v4?s=EEsb1kLbM5x5lYi4xKCs6%2F3Q3f7ZNYemNNbDoniajpvdVoz0iZDBqgNL6dIJzgD0D8c49rpdhnJlNhIIsHcFMlJomm4ktQDzbI100X8%3D"}]}
[19] => cf-cache-status: DYNAMIC
[20] => Nel: {"report_to":"cf-nel","success_fraction":0.0,"max_age":604800}
[21] => Speculation-Rules: "/cdn-cgi/speculation"
[22] => Server-Timing: cfCacheStatus;desc="DYNAMIC"
[23] => Server-Timing: cfEdge;dur=5,cfOrigin;dur=103
[24] => CF-RAY: 9d74f52d28b0ec6d-SIN
[25] => alt-svc: h3=":443"; ma=86400
)
789
报导/张健欣
摄影/董坤铭
视频/梁僡育
10月15日,国际白杖日。拄着拐杖前行,步调落了节拍,但不同的速度,一样可以奏出动人的生命乐曲。意大利著名男高音Andrea Bocelli、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萧煌奇,甚至新出炉的《美国达人秀》冠军Kodi Lee,都用鹤立鸡群的个人魅力,让观众忘了他们身上的残缺。每年今日,普天同庆,也许老天把你的灵魂之窗关上,是为了让你通过另一扇窗,收获更赏心悦目的风景。

(左)林友谊(35岁)—圣尼古拉盲人院、 电脑与科技导师
马来西亚盲人协会(吉打/玻璃市分会)主席。
(右)葛玛蒂Gomathi Supramaniam(35岁)—圣尼古拉盲人院 盲文书籍编撰者、马来亚大学 马来语研究学士学位。
上天从你生命掠走了光,你心里却有一把指南针,永远指向亮光所在之处。失明15年,几乎忘了天空的模样,于是你用手中白杖,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
青光眼夺走视力 但没有拐走他的聪慧
熹微晨光,透过叶片缝隙,洒在了宿舍。摇曳的光影,他无法看见,却隐约感受到,阳光递来的暖意。昨夜下了场雨,气温较低,他拿出的电饭锅,锅身是冰凉的。
“美好的一天,就要从下厨开始。”林友谊抛下白手杖,凭着对环境的熟悉,引领我们走到厨房。
20岁看不见至今,他拥抱了很多兴趣,其中之一就是烹饪。走在他身边,出乎意料地,很有安全感。从插电源到洗菜、切菜、倒入食材、控制水量,他办事有条不紊,马铃薯皮削得比我好。但不知何故,甫拿起胡萝卜,原本满心欢喜的他,倏地皱起了眉头。
“胡萝卜皮难削,一不小心就把萝卜芯给刮走了。”风趣横生的他,装耍脾气,把胡萝卜搁置一边,换成红番茄。顷刻,又见他笑逐颜开:“还是番茄好处理,只需几秒时间,轻易切成四段。”
青光眼夺走了他的视力,却没有一并拐走他的聪慧。ABC汤熬成后,林友谊仍乐不思蜀,热情地说:“下次再给你们煮肉骨茶,煮咖喱鸡。”说毕,问我们能否为汤拍张照,好让他发给母亲大人“评分”,令人莞尔一笑。
善良正向,是一种世界通用语言,它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。幽默机智的林友谊,人如其名,轻易与人搭起友谊的桥梁。在他的睿智领导之下,由担忧堆砌而成的心墙,一次又一次被铲为平地。
墨镜形影不离,是迫不得已。缓缓把眼镜摘下,眼白与常人无异,眼珠却呈浅灰色。刹那空气凝固了,看我们沉静了片刻,林友谊倒是笑了笑,自嘲化解尴尬:“是不是很吓人叻?”在这场情商较劲中,必须承认我们败得一塌糊涂。
好奇问他,盲人的眼里,是否如传言般,只得一片黑暗?他思考了片刻,认真回答:“患青光眼的起初,无法辨清颜色,但可以看到物体。渐渐地,视觉走向了死胡同,但可以感觉到光影。借由声音的回响,推断物体的距离。”
我把眼睛闭上,手掌面向眼,前后移动。隐约的光影,扑面而来的气流,仿佛找到了那感受。
午后,阳光正好。他腕上的智能表,轻声提醒:“现在是正午12时。”这位电脑与科技导师,把我们带到盲人院电脑室,分享用触觉与听觉学电脑的攻略。
 林友谊熟练示范,如何借由屏幕解读器,完成各项电脑任务。
林友谊熟练示范,如何借由屏幕解读器,完成各项电脑任务。
他解释:“键盘上的F、J字母与右方的5,底下都有条凸起的横线。这项全球统一的键盘设计,方便盲人在使用键盘时,辨认字母与数字的位置。”
另外,语音报读软体(Non Visual Desktop Access, NVDA)的使用,也让盲友可以完全掌控屏幕,通过电脑完成更多可能性,包括电邮、写履历表、阅读文章、社交媒体,使用微软办公软件。
“在6个月课程中,你会掌握超过1000个键盘快捷键,例如基本的全选Ctrl A,为字体上线条的Ctrl U等。”
换上工作服的林友谊,和下厨时候判若两人,每个指示都振振有词。学识渊博的科技达人,不仅是电脑导师,更练就了修电脑技能,偶尔施技赚取外快。
若能重新看得见,睁开眼的瞬间,他最想看见什么?林友谊说,他刚买了一栋公寓单位,想看看新家的面貌。为此,大伙儿浩浩荡荡,驱车往丹绒武雅,参观新房。
坐在轿车后座,林友谊虽然看不见,却可以清楚指引方向。经过两个路墩后,他可以清楚告诉你,接下来要拐左了,仿佛脑里装置了导航系统。车子若驶得慢,他还会关心问:“今天路上塞车了吗?”
出生于玻璃市的他,平时回乡独自搭巴士、坐渡轮,这些对他仅是鸡毛蒜皮。2012年,他获选参加DUSKIN国际领导培训课程,一个人搭飞机远赴日本,还在国外独立生活10个月。失去视觉,旅游不是梦。于工作或旅游,北京、曼谷、印度、台湾、新加坡,他都曾到访过。
“多得智能手机的屏幕解读器,平时我可透过Food Panda叫外卖,也可以自行搭GRAB,轻松前往目的地。”
旅游、事业、买房,听起来几近完美,那人生还缺什么?
林友谊脸上一沉,放低了声调:“其实失去视觉后,我曾谈过两次恋爱,但基于女方父母反对,恋情都无疾而终。最大的心愿,大概是找个伴侣,一生相伴。”
每颗向善的心,终会走向亮光之处。真心祝福,步上红毯的那一天。
“若能重获光明,最想看见新买的公寓单位。或许找个伴,在此依偎一生,就更完美了。”
 相比起许多视盲者,葛玛蒂的眼珠看起来和常人无异,这让她在公共场合寻求协助时常碰钉。
相比起许多视盲者,葛玛蒂的眼珠看起来和常人无异,这让她在公共场合寻求协助时常碰钉。
如果不曾看得见,这地球是圆是方,是否真的那么重要?就像你不曾学会飞,有天赐予你一双翅膀,那未必是一份美好的礼物。
和瑕疵共存 过自己的生活方式
从葛玛蒂身边走过,压根儿不会察觉,她是一位B1全盲者。眼睛炯炯有神,眼珠黑白分明,在她眼前晃了晃手,还真的没眨眼,才确认了她的失明身份。
经过深谈,方才发现,已不是第一次被误解。这位印裔女生笑言:“我刚出世的时候,眼睛看起来就无恙,就连妈妈都没发现,我双眼是看不见的。”
“后来开始学走路,步伐战战兢兢,母亲觉得有些不对劲,才把我送到医院检查,得出我有视觉障碍的结论。”
接下来的故事,想必不难猜。为人父母自是难以接受,湿着泪眶四处寻医。原由没有弄出个所以然,只知道若有眼膜捐赠者,就有恢复视觉的希望。再后来,听说眼膜移植手术,或会造成后遗症,原本就安然无恙,葛玛蒂想不到一个要转变的理由,于是决定和瑕疵共存,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走下去。
“有时候搭巴士寻求帮助,被人误以为看得见,都无奈不受搭理。”她耸了耸肩,继续述说一则又一则糗事。
来到圣尼古拉盲人院,葛玛蒂在盲文键盘前,用心执行校对工作。只见她俐落把一段英文字,通过翻译软件“Duxbury”译为布莱叶盲文,接着开始逐字检查与纠正。
“如今科技先进了,我们不用盲文打字机了,都转为和电脑相连的盲文键盘。”
在这家非政府组织工作6年,她总共制作了上千本盲文书籍,当中包括学校参考书、小说、宗教书籍和各类文章等。葛玛蒂表示,一本正常的课本,相等于盲文的5本书,可见工作不简单。同时,她还是一名盲文导师,教导视觉障碍者触摸与阅读盲文。
“在圣尼古拉,公司对我的工作评估,与视觉正常者无异。生病必须请病假,根据工作表现加薪等,这样的工作环境让我感到舒服。”
来自吉隆坡的葛玛蒂,如今居住在盲人院宿舍。每隔两个月,她都会自搭巴士回乡,讶异问她是怎么办到的?
“通过手机的屏幕阅读器,我可以自己搭GRAB到巴士站,再从那里搭巴士到吉隆坡中央车站。”
这名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姑娘,笑称前两次母亲带她走遍巴士站,后来她就把方向大图给记住了。在几番误打误撞,以及善心路人的协助之下,如今她已有能力单独搭巴跨州。
出生至今看不见,有否想过世界是什么模样?葛玛蒂说,既无法突围想象,也没有多大期待。现在的她,即使孑然一身,却过得很自在,从没把自己当失明人士看待,还在马来亚大学考获马来语研究学士学位。
“分不清普腾和丰田,其实也没关系,我对现状感到满意,也沉浸于对工作的热爱。”语毕,脸上露出灿烂的笑靥,仿佛残疾不曾在她身上存在过。
“我没看过这世界,对它没有多大的憧憬,现在的我过得很好,再看得见也未必是锦上添花。”
找工作, 就找这里!

› 立即申请
- GMBB Part Timer
- Event
- Kuala Lumpur
-

MYR 11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Social Media Marketing Executive
- Advertising & Market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6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Software Develop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Wilayah Persekutuan
-

MYR 6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DevOps Software Engine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6.5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Java Software Engine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10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软件测试与客户支持专员 Software Testing & Customer Support Specialist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3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Software Developer
- Information Technology
- Kuala Lumpur
-

MYR 4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Software Engineer (Internship)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HR Recruiter (Internship)
- Human Resources
- Kuala Lumpur
-

MYR 85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Software Engineer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4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Web Developer (Internship)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Admin cum Customer Service
- Engineering
- Bayan Lepas
-

MYR 3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PHP Web Developer
- Engineer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4K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Multimedia - Video & Marketing (Internship)
- Advertising & Market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
› 立即申请
- Graphic Design + Marketing (Internship)
- Advertising & Marketing
- Kuala Lumpur
-

MYR 800.00 /Month
//
//
//
//